
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研究展望
来源:王灿,邓红梅,郭凯迪,刘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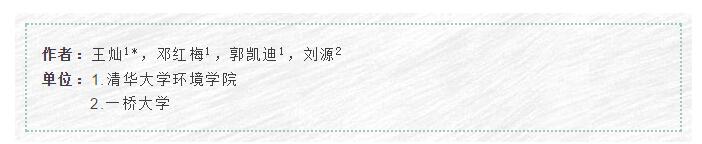
摘要: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是一种双赢的策略。自协同效应的概念提出以来,大量研究对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之间的协同减排技术、措施、潜力等方面进行了评估。本研究回顾了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典型案例以及重要的政策实践,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当前研究与实践的特点,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典型案例涉及能源、交通、工业和居民部门,政策实践讨论了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的主要类型及其实施情况。从损失评估、协同机理、高精度排放清单及模拟等角度对未来促进协同治理的研究提出了方向建议。
我国当前面临的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任务,需要同时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推动下,我国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但由于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运输结构偏油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臭氧、硝酸盐、铵盐和黑碳等大气污染的防治任务仍然艰巨。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200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013年中国人均碳排放达到了7.2吨,超过了欧盟的6.8吨。2015年6月,中国为推动《巴黎协定》达成,提出了“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等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我国能源消耗型工业占比较高,城镇化过程仍在持续推进,预计短期内仍有大量的能源消耗需求。同时,产业升级、非化石能源体系的建立和推广等过程耗时长、成本高。在此背景下,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较大。
在严峻的现实需求和积极的宏观政策号召下,深入探讨我国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协同治理有利于降低大气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总成本。从长远来看,要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的目标,必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升级。而短期内由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靶向更明确,管控更严格,如果不考虑协同作用,企业会倾向于选择采用短期内效果更显著的末端处置设备。相比于协同情景下实现路径的一次全局优化,无协同情景下的二次决策很可能会带来成本浪费,甚至增加治理费用,例如,燃煤电厂的末端脱硫措施将增加CO2排放,燃煤电厂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也将因其自身的电力消耗而引起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其次,进行协同治理有利于避免高碳锁定效应。以一次能源消耗和高耗能行业引领的工业发展路径在促进我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工业行业排污比重高的现状。单独的污染排放管控,有可能将解决方案锁定在相对高效的末端治理技术上,从而削弱低碳转型的动力,产生进一步的高碳锁定。
1 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概念的起源及发展
20世纪90年代已经有相关学者对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进行了初步研究。Ayres和Walter论述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和效益,指出了其间接效益包括空气污染物的减少及其产生的相关健康效应。Messner探讨了减排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协同效应和相关政策冲突。关于协同效应(co-benefits)的定义源于2001年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协同效应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同时实施的政策所带来的效益,它包括了气候变化的减缓,并且承认很多温室气体减缓政策也有其他甚至同等重要的目标,如空气污染物的减少”。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还将协同效应(co-benefits)的概念和在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中出现的副效应(ancillary benefits)进行了区分。协同效应是指在政策设计中被明确提及的目标,而副效应是指随着主要政策附加出现的一些其他效应。
随后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和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对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政策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IPCC第四次报告进一步指出协同效应的概念通常也指“无后悔”政策,这是由于很多项目和行业的减排成本研究已经识别出了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具有潜在的负成本,即实施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协同效益会大于其实施成本,因而这些具有负成本的减排政策通常被称为“无后悔”政策。相关研究显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所带来的空气污染减缓协同效应不仅可以改善人体健康状况,而且也会对农业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这种近期可见的效益为“无后悔”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将协同效应区分为了积极的协同效应和消极的协同效应(不利的副作用)。该报告探索了温室气体减排路径的技术、经济和制度需求以及相关的潜在积极协同效应或不利的副作用。2018年发布的《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则将协同效应的概念进一步聚焦在积极影响上:“协同效应是指实现某一目标的政策或措施对其他目标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而增加社会或环境的总效益”。协同效应的评估往往会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并取决于当地具体的外部环境和政策实施条件。
2 终端部门协同治理的主要路径
很多研究往往以孤立的视角单独聚焦全球气候变化或者局地空气污染问题,但是这两类不同的环境问题却紧密相关,大多都是由相同的能源生产或消费模式所驱动,因而亟须设计相关政策对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进行协同控制。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温室气体减缓政策可以产生空气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减排空气污染物的政策也会产生减排温室气体的协同效应。此外,也有整合了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物的综合性政策同时考察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效果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很多的研究文献都在定量地评估减排温室气体或空气污染物所产生协同效应的大小。从部门层面上来看,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协同治理的主要部门包括能源部门、交通部门、工业部门和居民部门。
能源部门是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局地空气污染贡献都较大的一个行业,化石能源的燃烧同时驱动了这两种环境问题的排放。在能源部门治理这两种环境排放行为的减排政策通常也是单独实施,例如,针对煤炭发电厂的碳捕集与碳封存(CCS)技术,但它仅会减少CO2的排放,却不能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而常规大气污染物(NOx、SO2、PM)通常采用末端治理技术进行治理,但此技术并不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能源部门协同治理的实现措施主要集中在发电效率的提升和发电结构的优化。发电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淘汰小型低效的火电机组,新建大机组以持续降低发电煤耗;发电结构的优化主要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并降低煤炭发电的占比。发电产生的大气排放的影响取决于发电厂的空间分布和电力调度决策,对低碳电力空气质量影响的评估必须考虑到相关排放的空间异质性变化。低碳电力政策所产生健康效应的货币化价值可以抵消掉很大一部分气候政策的实施成本,有些能源政策的健康效益值甚至还会超过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
交通部门是许多区域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且全球交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约占25%。虽然交通部门也存在同时解决两类环境问题的措施,但是很多国家往往更强调解决其中的一种环境问题,而不是致力于探寻双赢的解决方案。因此,很有必要加强对交通部门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治理的认识。交通部门主要包括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等交通方式,其协同减排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的措施包括:能效的提升、交通出行模式的转变、建设紧凑的城市形态和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等。交通部门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特性不仅被全球层面的研究所证实,也被应用于首尔、波哥大、伦敦和墨西哥城等城市层面的研究中,并考察了交通部门大气减排的多重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工业部门包括化工、钢铁、水泥、铝、纸张的生产以及矿物开采等行业。目前工业部门的大气减排措施主要包括通过新工艺和技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强度、减少产品需求、提高物料利用率和回收率等。全球很多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都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减排技术相对落后,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例如,Thambiran等评估了南非德班工业部门的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政策,研究发现,当炼油厂从使用重燃料油转向使用炼厂气和富含甲烷的天然气时,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两类环境问题的协同减排。水泥行业也是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污染源,中国各省份水泥行业不同碳减排技术产生的空气质量协同效应具有很大差异性,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和较为富裕的省份,空气质量的协同效益较为显著。将空气质量协同效应考虑在内,会大大降低碳减排的社会成本,因此,区域协同效益的识别是优化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设计的关键。
居民部门包括供暖、照明、烹饪、空调、制冷和其他电器的使用等。居民部门的大气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和能源的消耗,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家庭使用的燃烧效率低下的传统固体燃料和生物质燃料等。一些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如改进炉灶,改用更清洁的燃料,改用更高效、更安全的照明技术等,不仅可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可以缓解因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问题。通过燃料替代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的散煤使用是中国居民部门实现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的关键。Wilkinson等人指出,在印度全国实施促进现代低排放炉灶技术的计划,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效益。Jamison等人评估了在世界不同地区实施的旨在减少使用固体燃料做饭或取暖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等特定干预措施的实施成本及其健康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只要能够大幅减少在室内空气污染中的暴露,这些干预措施就具有成本有效性。虽然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实施一系列能源创新项目,但特别需要集中精力实现发展中国家家庭能源系统的改善,从而减缓发展中国家居民因室内空气污染而引起的健康损害。
3 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的政策实践
发达国家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历程有两个明显特征。首先,治理周期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过程较为和缓。无论是提高大气污染物管控标准还是进行能源结构新旧转换,欧美企业都有较长的适应和升级周期。其次,不同时期内,政策重点主次特征明显。20世纪发达国家在进行空气污染防治时,气候变化问题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21世纪发达国家着力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但空气污染问题已经不再突出,因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协同效应研究大多集中在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所产生的局地环境效益。
不同于已经基本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和实现能源、产业结构转型的发达国家,尚处于城镇化过程和经济结构转型的中国面临着外部催熟和内部夹生的尴尬矛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和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相比长期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短期内在我国进行空气污染治理有更为严峻和紧迫的现实需求。因此,当下的协同控制应以空气污染治理为主要目标,并同时考察由其所产生的减排温室气体的协同效应。目前我国主要的协同治理措施可以概括为目标协同、路径协同和监管主体协同。
3.1 目标协同
从国际经验来看,从污染物单一治理到多种污染物综合治理是空气质量管理实践进程中的必经之路。中国同时采用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政策体现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治理措施的目标协同。
中国采取的命令控制型政策在于不断完善大气污染物和碳强度的控制指标。中国从“十五”期间开始管控SO2排放量,但计划期末的SO2排放总量不减反增,这促使我国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节能减排措施及环境约束指标;“十一五”规划中规定了SO2总量与单位GDP能耗的降低比例,并首次把SO2排放量纳入国家约束性总量控制目标;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所以“十二五”规划中新增了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比例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这两项指标,另外主要污染物的控制目标中还新增了对NOx的总量控制,“十二五”规划直接体现了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两方面的治理目标;“十三五”规划中将O3和PM2.5的前体物VOCs纳入减排的预期性指标,此外,还新增了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和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这两个约束性指标,反映了我国环境治理从总量控制到环境质量改善的转变。总体而言,我国逐年完善的国家规划目标反映了政府加强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治理的理念。表1中列出了我国历次“五年”计划/规划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总体控制指标。

中国还采取多样化的经济激励政策促进污染物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如鼓励发展环保产业、推进排污权交易和排污收费、设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和深化碳市场建设等。2011年,中国在7省份推行碳交易市场试点计划,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首批纳入了发电企业,并计划逐步扩大实施范围。
3.2 路径协同
我国通过推进清洁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能源结构,探索了大量可以实现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治理的技术路径及政策措施。
清洁生产的全过程控制强调源头和过程监管,识别和分析污染源的产排特征及影响因子。目前我国主要通过采用先进工艺和技术降低产品能耗、提高物料利用率和回收率等措施实现协同减排,如通过推广循环流化床燃煤发电、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等高效燃煤发电技术提高能源加工转化效率;水泥行业采用新型干法水泥减少单位水泥燃烧排放的CO2,利用工业废渣、低热值燃料及可燃废弃物替代熟料降低能耗;钢铁行业提高废钢使用率、增加电炉钢比例等。
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7年和2018年先后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实现化解钢铁过剩产能超过5500万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2.5亿吨。行业层面紧抓能源消耗大户,电力生产部门占据了约50%的煤炭消耗量。从“十一五”时期起,政府开始加强对电力部门能源节约和污染减排的综合管控,包括发展清洁能源、推广热电联产、鼓励加装能源节约装置等措施。
在优化能源结构方面,中国严格控制煤炭消费,连续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关于加快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促进北方采暖地区燃煤减量替代的通知》等政策,推进煤改电、煤改气和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改造等措施;政府还大力推进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建立完善优先发电制度,发布《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等指导文件;发展非化石能源也是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举措,《国家能源局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探索用市场机制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3.3 监管主体协同
我国监管部门职责分散化、行政管理条块化的特征对协同控制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管带来了不利影响。生态环境部的成立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些局限,缓解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治理的制度障碍。2018年以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分别由原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两个部门牵头负责。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08年机构改革中设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司,其主要职责包括综合分析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组织拟订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牵头协调、组织和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具体工作。由两个独立部门分别负责大气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减排,在政策制定时难以综合考虑政策的协同作用,在政策实施时部门联动的政策实施成本高、运行效率低等问题都阻碍了深度协同控制的有效实现。2018年,原环境保护部改组为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整体转隶到生态环境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统一负责”和“大生态监管”时期。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防治部门的隶属统一将大幅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机构间的协调成本,并促进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
具体实施层面,推进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5年重点工作》将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唐山、廊坊、保定、沧州一共6个城市划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区,开展清洁取暖、淘汰燃煤小锅炉、压减过剩产能、淘汰黄标车与老旧车等减排措施,密集发布的环保政策和雷厉风行的铁腕管制措施改善了中国区域空气质量并有效抑制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另外在城市层面,低碳试点、新能源试点等项目也鼓励了自下而上的协同管理和创新。
4 已有研究的特点和展望
关于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已有大量研究,涵盖了主要排放行业,为推动协同治理的政策实践和技术研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方向,但仍存在大量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1)行业不同政策情景协同效应的量化估算较多,但是缺乏将协同效应整合进政策设计或优化改进的案例研究和实践指导。空气污染减少的协同效应仅作用于当地并且是短期的,而气候变化减缓的协同效应具有全球性且是长期的,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优先级差异可能会扭曲政策优化目标的设定并导致次优的控制策略被采用。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协同治理措施在很多场合被忽略的原因主要包括:环境问题的空间和时间属性不同,气候变化的损失及其减排成本存在不确定性;协同效应的衡量结果对评估方法和参数的选择很敏感,如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偏好因收入差异而不同;科学和政治领域的制度障碍也阻碍了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的协同治理等。
(2)在协同减排技术评估和方案研究中,对技术供给侧减排成本改进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对协同减排所带来的需求侧间接效益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文献虽然综合考虑了协同控制策略的成本和收益,但是对于协同效益的评估大多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的,缺少对区域和城市层面的精准研究。由于空气污染物是局地环境问题,更精细的空间划分可以帮助地方制定更具操作性和成本有效性的协同控制政策。
(3)需要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进行统一框架下的量化和整合。空气污染是当今造成疾病和死亡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气候变化会增加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如热浪、野火、风暴、洪水和干旱等都会增加疾病负担和过早死亡。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量化研究逐渐增多,但在暴露水平、健康损害的货币化等方面仍缺乏必要的指南以确保不同案例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同时,将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进行协同考虑也存在方法学上的一些障碍,例如时间尺度的一致性、代际公平的考量、生命统计价值的可比性等问题。
基于以上现状特点,未来协同治理的研究需要在以下4个方向取得突破进展:
第一,针对既影响大气环境质量又产生显著温室效应的污染物(例如黑碳、某些氢氟碳化物等短寿命的气候变化污染物),提高其减排和治理的优先序。这类污染物来源复杂且往往伴有共生物质的排放,需要识别其排放清单并研判未来排放情景、提出精准控制手段和有效减排技术,为低成本实现尽可能大的协同治理潜力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第二,将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纳入协同治理技术和路径的综合评估。气象条件会影响空气污染物的形成,因此气候变化可能会间接影响空气污染。一些大气化学模型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未来的气候变化可能会使空气质量恶化,即所谓的气候惩罚效应。但是极端气候对未来空气质量和相关健康影响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也很少被量化。同样,大气污染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气候变化。例如,微颗粒物既可以通过短波辐射(硫酸盐和有机碳粒子)的散射产生冷却作用,也可以通过短波辐射(黑碳粒子)的吸收产生气候变暖的影响。除了散射或吸收的直接影响外,微颗粒物还可能通过影响云层以及雪和海冰的反照率来间接影响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通过大气的化学作用联系在一起,一些空气污染物也会影响温室气体的寿命。两者的相互影响最终将改变对协同治理技术和路径的认识。
第三,综合评估协同减缓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的经济价值。对于大气排放所产生的损害对象包括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等,目前还缺乏对这些损失全面衡量的经济度量研究。目前对人体健康的研究大多聚焦于PM2.5的健康损害,虽然一些学者也研究了臭氧(O3)的健康影响,但是数量相对较少。O3是NOx和VOCs在阳光下合成的产物,尽管一些研究指出O3浓度的增加会产生短期的健康影响,但是几乎没有证据显示O3会在长期内对人类疾病和过早死亡产生影响。而CO虽然在高浓度下会致命,但是其在正常大气暴露浓度下的健康影响较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是SO2和NOx产生的酸沉降,通常也称酸雨,它会对森林、水生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如氮氧化物的酸沉降促进了某些河口有害藻类的繁殖,SO2和O3可以使一些庄稼和树木的树叶坏死,因此会影响农业和林业的产量。空气污染造成的其他社会影响包括降低可见度,对建筑、雕像和纪念碑产生腐蚀作用等。这些健康、生态及社会方面的损害都需要对其经济效益进行更深入地评估。
第四,构建高精度的排放清单和模拟系统,在高精度的空间上识别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技术和协同治理策略。已有文献基于高精度网格化的污染物排放清单研究了全球和区域层面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协同考虑减缓气候变化时,还需要解决长期社会经济发展情景的空间化问题。为此,既有模拟系统建设的方法学开发需求,也有未来长期情景空间数据的基础性研究需求。


